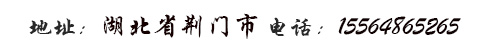王爱松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
|
王爱松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小说叙事学”。 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 众所周知,互文性的概念是由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最早提出的。但按克里斯蒂娃后来的回忆,这一概念仍可追溯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她自己的贡献是将巴赫金的“一种话语中有数种声音的观念代之以一个文本中有数个文本的观念”[1]。按克里斯蒂娃的最初解释,所谓互文性,就是“所有文本都将自己建构为一种引语的马赛克,所有的文本都是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化。”[2]文本是一种生产力,是数个文本的一种排列组合,互文性即是“在一个特定文本的空间中,取自其它文本之中的几种话语相互交叉和中和”[3]。互文性的概念后经罗兰?巴特、热拉尔?热奈特、米歇尔?里法台尔的引申和发挥,已衍变成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时髦概念。特别是,由于罗兰?巴特在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的基础上将文本视为“一个各种写作其中没有一种是本源性的在其中混合和冲突的多维空间”,“一种引自无数文化中心的引语构成的织品”,并且颠倒了以往文学理论中作者与读者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提出了“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4],互文性概念在提供了更多洞见的同时,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 与国内对互文性理论渐成气候的翻译、介绍和评述相比,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互文性现象的研究迄今还不充分[5]。本文拟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互文性现象做一初步清理,并考察互文性理论给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创作和研究提供了何种洞见,以及有可能遮蔽何种问题。 一 理论界对互文性的研究,大致采取两种路径。一种更侧重于实践的研究,强调一个特定文本与其前文本间的联系,即像叙事学家普林斯那样,将互文性理解成“一个特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重写、扩展或从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间的关系”[6],认为文本只有在能够明确验证和指出其间存在着引用、仿写、暗指等等形式时,才构成互文关系。另一种路径更侧重于理论的研究,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为代表,他们持一种更宽泛的互文性观念,强调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本,文本被视为“引语的马赛克”。本文试图先采取第一种路径,清理中国当代小说中可验证的互文性现象,继而在此基础上沿第二种路径对相关理论问题略加探讨。 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互文性,一个最直接的标准是看一个特定的文本是否指涉另一个文本或多个文本。按戴维?洛奇的看法,“用一种文本去指涉另一种文本的方式多种多样滑稽模仿、艺术的模仿、附合、暗指、直接引用、平行的结构等。”[7]在读者的阅读审美活动中,面对一个小说文本,文本的标题是否指涉另一文本,通常会成为读者判断该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是否构成互文关系的最直观依据。王安忆的《天仙配》,其标题让读者立即联想起民间传说“天仙配”须兰的《石头记》,其标题让读者联想起《红楼梦》格非的《锦瑟》,其标题让读者顺理成章地联想到李商隐的《锦瑟》而李修文的《王贵与李香香》,其标题也同样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李季的诗歌。这种由小说标题所直接建立起的互文性,在当代文学中极为普通。 热奈特曾将标题的功能区分为四种:命名或辨识功能;描述功能;暗示功能;诱惑功能[8]。命名或辨识功能是每个标题唯一必须具有的功能,虽然给一部作品命名,就像给一个人命名一样,有其任意性和偶然性,由于同名现象的存在,甚至命名和辨识的功能事实上也不能毫无歧义地由一个标题单独完成,但在周边语义的压力下,甚至最简单的作品编号也可能充满意义。描述功能涉及到对作品主题、素材及文类等的指示和描述,又可细分为主题性功能、述位性功能和主题性与述位性相结合的混合功能,这种描述功能在理论上并不是每一标题必备的,但在实际中往往难以避免,通常会成为读者阐释的钥匙。暗示功能是附着于主题性功能和述位性功能的语义功能,即在描述功能起作用时,还包含了其它隐含的信息和价值。热奈特曾特别提到了由引语构成的标题(quotation-title)、拼贴性标题(pastiche-title)、戏仿性标题(parodictitle)所具有的暗示功能和文化效果它们都是一种共鸣和回响,“为文本提供了来自于另一文本的间接支援,以及文化传承关系的声望”[10]。 毫无疑问,不管作者在命名时是有意还是无意,具有互文性的标题都或多或少具备热奈特所说的一般标题所具有的功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标题的一个特殊之处,是提供“间接资源”的文本成了读者购买、阅读、评价后文本的一个重要参照和背景。尽管王安忆的《天仙配》写的完全是一个现代故事———穷乡僻壤的夏家窑的村民,以乡俗完成了为村打井意外死去的孙喜喜与解放战争时期因伤牺牲的小女兵的冥婚———但标题“天仙配”仍引起读者对这一冥婚故事与古老的民间传说“天仙配”有何异同的好奇和思索。同样,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所写的王琦瑶的故事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毫不相干,但标题本身仍然会激起读者对作者为何要取这样一个现成标题的兴趣和沉思。至于李冯《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格非《半夜鸡叫》等小说由标题本身所透露出的特殊戏谑气息,更是以构成互文性的另一文本或另一些文本的存在为前提。 章、节、段的标题(乃至更大的部、编的标题),理论上能起到与一部作品的总标题大同小异的效果,只不过发挥作用的范围比总标题要小,读者也只有在翻开作品、进入实际阅读或浏览过程中才能逐渐接触到它们。热奈特曾将章、节、段、编等的标题统称为内标题(intertitle)。并不是所有的内标题都是我这里所研究的对象,只有构成互文性的内标题才是这里所要考察的。理论上说,在内标题出现的位置,并不必须需要出现内标题,更不必须出现构成互文性的内标题。现代作家以简单的章、节、段等的数字编号即可标识作品的篇章结构,完成作品章节等的转换。然而,具有互文性的内标题的出现,不仅承担了指示作品篇章结构划分的功能,而且带来了其他诸多文本的附加信息。杨绛的《洗澡》共分三部,分别为“采葑采菲”、“如匪浣衣”和“沧浪之水清兮”,取自《诗经?邶风?谷风》、《诗经?邶风?柏舟》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流传的民歌《孺子歌》:在一部白话文小说中引用古奥的诗和民歌句子作为内标题,无疑形成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但同时也达到了对作品中姚宓、许彦成等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态的高度暗示或概括,并进而引导着读者的阅读与阐释。阎连科的《风雅颂》稍有不同。该书共分12卷,卷下再各分若干章。各卷分别以“风”、“雅”、“颂”或“风雅之颂”作为标题,而卷下各章全部由《诗经》的某一篇名加上概括该章内容情节等的一句白话构成。这种标题方式使《风雅颂》整体上与《诗经》产生了明确的互文关系,一方面呼应了文中主人公杨科的《诗经》研究者身份,另一方面也使文/白、古/今两个世界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映衬,构成了一个明显的对话空间。无论总标题还是内标题,到了现当代的小说创作中,都要求简洁。或许正因为这种约定俗成的要求,使中国当代小说家在设计自己带有互文性的小说标题和内标题时,更多地求助于古代作家作品。但借用现当代作家作品的例子也不是完全没有。马原的《游神》最后一章的标题为“结局或开始”,并且在该章的开头直接点明“借我的朋友北岛的诗题”,这就在《游神》和北岛的《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之间建立起了互文关系———只不过,在北岛那里,“结局或开始”承担的更多是主题性功能,而在马原这里,承担的更多是述位性功能:他在通常小说标明尾声和结局的地方,借用北岛的诗题,来表明自己作品结尾的开放性,以区别于传统小说结尾的封闭性。 利用题记建构互文性也是中国当代部分小说家爱用的手法之一。无论全文或全书的题记还是各章节的题记,往往会对作家的创作意图、作品的主题内容、故事情节以及阅读方法等起重要的指示或暗示作用。当然,只有具有文本互涉特征的题记才能成就互文性。以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为例,该作引用了拉格洛孚的一句话作为题记:“当然,信不信都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这一题记初一看,与普通题记特别是采用全知叙述的小说的题记并无本质差异,似在宣示叙述者至高无上的上帝般的虚构权力。然而,这一题记同时还建立起了该作与拉格洛孚、福克纳等所写的猎熊故事间的互文关系。“我不说你猎熊的故事,有那么多好作家讲过猎熊的故事。美国人福克纳,瑞典人拉格洛孚,还有一部写猎熊老人的日本影片。”《冈底斯的诱惑》中讲述穷布的故事的叙述者如是说。自称不讲穷布猎熊的故事,但最终还是讲了穷布与熊的故事,这里透露出的正是布鲁姆所说的后代作家在面对前代作家时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具备互文性特征的题记有时是指出创作的灵感来源,所受的直接、间接的影响,有时是涉及文本的主题内容、故事情节、结构关系或阅读方法,对读者的阅读起到一定引导作用。以王小波《红拂夜奔》第六章的题记为例,该章不仅有位置在章节之前的题记,而且有位置在章节序号之后的题记。章前题记明确写道“本书这一部分受到了乔治?奥维尔的经典之作《》的影响。有人说,《》受到了摩尔爵士《乌托邦》的间接影响。假设如此,本书作者就是从这两本书内获得了益处。”章节序号后的题记则直接点明本章内作者提到了自己年轻时当司务长的事“假如不是满脸苦相,骨瘦如柴,那个时候他有点像好兵帅克的模样。”如此说来,《红拂夜奔》不仅与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存在互文关系,而且至少还与乔治?奥维尔的《》、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雅?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存在互文关系,真正构成了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具备互文性特征的题记,更多时候是以直接引用其他作家作品的某句话或民歌、民谣、名言之类的形式出现。这种直接引用,无论有没有标明具体出处或标注的详略程度如何,实际上是一种出现在题记位置的引语,所承担的文本互涉的功能通常大同小异。这里更值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eixingzhao.com/fxzzp/4996.html
- 上一篇文章: 真值得收藏耳鼻喉知识汇总常德耳鼻喉医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